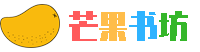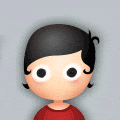姜宁告别陆掌柜,从酒楼出来,发现外面不知何时又下起了雪。
微微怔愣片刻,随后转身正欲回去拿伞,头顶忽地多了一把伞。
他一惊,回头看去,就对上卫长昀的目光。
脸上惊讶的表情变成笑意,瞥他一眼,从容走到他身边。
“怎么来了?”
卫长昀举着伞,与他并肩一起走,“正好在这附近办完事,时辰也不早,就过来接你一起回家。”
“案子一切顺利?”姜宁问:“今日酒楼可让人闹事了,恶性竞争。”
“听说了,人送到官府去。”卫长昀点头,“你怎么认得那只蛐蛐?”
姜宁低咳一声,努努嘴,“从前在家里,我不是看了许多闲书,里面便有这个。”
“不只是书,不还有一些画本吗?画得可好了。”
卫长昀失笑,侧过头看他,“这就是你说的,学到的知识总有一日能用上?”
姜宁煞有介事地点头,“自是。”
“贪墨案能抓的人都抓了,你与我说的那些,我们一一审过,又供出不少,只不过延州私兵一事,怕是控制不住了。”
卫长昀抬眼,看向街上百姓,“希望能过了这个年。”
姜宁怔住,“你的意思是——”
真的要宫变吗?
可既然知道有私兵的存在,为什么不直接先出兵剿灭呢。
“私兵这事,皇上还不知道,因为没有证据。”
卫长昀道:“延州军营看着安分守己,又是在大燕的领土内,如何能轻易发兵?”
这么一说,姜宁也反应过来。
天下尚且看着安定,用什么理由发兵?
一旦发兵,只会动摇民心。
“宫里情况如何?”姜宁担忧道:“只要宫里没事,便乱不起来。”
卫长昀轻叹,“几位太医已经常驻宫里,只有内阁李首辅、允王与几位尚书……以及老师能见到。”
姜宁啧了声,“也真是好手段,看似不见人,实际上人人都见了,把决定权又交给了别人,看谁先坐不住。”
利用自己的病情成为变数,又成为自己制衡各方势力的利刃,明德帝若是身体好些,倒也不至于有这些事。
“且不说这些事了,再有半月就要过年,你这儿不会除夕还在审犯人吧。”
姜宁伸手去牵卫长昀的手,晃了晃,又觉得冷,牵着一起缩回斗篷里。
“……应当不会。”卫长昀低咳一声,“如今案情已经明朗,整理清楚相关案件细节,还有各方的口供,待与刑部沟通后,便可以定案,走结案的程序。”
姜宁听着听着,不禁一笑,“你受我影响可是越来越大了。”
卫长昀不明所以,嗯了声,等着他下文。
姜宁眼波转动,“说话的方式呀,不过我对司法不熟,不然还能帮到你。”
“你已经帮我良多。”卫长昀摇头,“总不能事事都要依靠你。”
姜宁笑而不语,只嗯了声。
卫长昀不与他多聊案子的事,怕他为此担心,觉得困扰,转而说起了过年的事。
金陵是京城,过年自然是极为热闹的,各种灯会、诗会从除夕到上元节都有,城内百姓可以狂欢到深夜。
“这回可以全家都出来玩了,酒楼那边只要安排妥当就好。”
“除夕那日,周庚能不当值吗?”
“可以啊,之前中秋和重阳,他都在酒楼顶着,除夕该轮到到他了。”
“嗯,这便好。”
“放心,除夕那天酒楼只营业到亥时,亥时一到就不再接新客,放大家回去过年。”
闻言卫长昀一愣,姜宁看他表情,松开他手搓了搓。
“我们又不是压榨人的地方,虽说酒楼过年营业很正常,但赚钱是为了自己和家里人过上好日子,不让人回去过年可不行。”姜宁瞥他一眼。
卫长昀目光落在他手上,指尖被冻得通红。
往旁边扫了眼,正好看到有人在卖烤红薯,热气腾腾的。
“难得走回家,一会儿要不要买点李记的酱肉回去?”姜宁正说着话,伞柄忽地塞到手里。
“你去干什么——”
“等我会儿。”卫长昀交代一句,低头走出伞下,朝着卖红薯的老伯跑去。
姜宁怔住,盯着他背影,先是疑惑,等看到他去的方向,倏然笑起来。
卫长昀顾不得身上过于醒目的官服,有些急地问:“老伯,这红薯怎么卖?”
“客官要几个?大的十五文,小的十文。”老伯道:“要是买两个,给您一个便宜价,二十二文。”
“要两个,这是钱您收好。”卫长昀掏出铜板递过去,“麻烦您用油纸包一下。”
“得嘞,我这就给您装。”老伯麻利接下钱,揣好后,直接用手把红薯装进折好的纸袋里。
卫长昀接过来,向老伯道谢,捧着两个红薯跑回姜宁身边。
姜宁见他过来,立即把伞面仰起一些,看着他钻到伞下。
“给。”卫长昀把红薯捧到他面前,“拿着暖暖手。”
姜宁伸手去接,目光扫过他肩头的雪,“都给我啊?”
卫长昀重新拿了伞,“两只手。”
姜宁忍不住笑出声,强行把其中一个塞给他,“我这样捧着就好,哪用得着两个。”
卫长昀啊了声,就见姜宁已经在剥皮。
红薯烤熟后的果肉是橙红的,中间还有流心,松软的肉被掰开,香甜的味道立即散开,诱得人食欲大开。
姜宁一向爱吃这些,偶尔还自己丢几个土豆、番薯到灶孔边的灰里埋着,一顿饭做完,差不多就熟了。
低头咬了口,软糯的口感绵绵的,暖烘烘的,身上也跟着暖和了。
姜宁举起手,递到卫长昀嘴边,“你也尝尝,还挺好吃的。”
卫长昀自然低头咬了口,“下回想吃再来他家买?”
“随缘就好,总不至于为了口吃的跑这么远。”姜宁等他咬完,立即缩回手,“再说了,我自己也能烤。”
卫长昀笑道:“是,你烤得不比这个差。”
姜宁理所应当地点头,“那是当然。”
卫长昀撑着伞,留意着他的脚下,不时提醒或者拉他一把,等一路走到家门口,姜宁手里的红薯早就吃完。
“嗳,到家了,把伞收了吧,这雪——”姜宁拍拍手,转头去和卫长昀说话,便见他肩头湿了一片。
要不是有披风挡着,都该浸到衣服里去。
卫长昀把伞立在一边,解下披风搭在臂弯里,“不要紧。”
姜宁抿唇,抬眼盯着他,见他眼里笑意,心里一软又有些闷,“明天去买两把大点的伞。”
“听你的,明天就去买。”卫长昀牵起他手,“难得一起回来,看看幼安去。”
算算时间,孩子的百日宴快到了,也就是除夕前一日。
到时候得安排抓阄的东西,还有一些百日礼。
尽管有朱红和春娘、方管家一块张罗,但为人父亲,总不能一点都不过问吧。
“百日宴上抓阄的东西,你打算放什么?”姜宁和他并肩走在廊下,好奇问了句,“我还未想好。”
抓阄时,每个人只能放一样东西,所以得选。
姜宁倒是想直接把一锭银子上去,这样一手抓财一手抓健康,反正猜都猜得到朱红一定会放平安锁。
“我以为你会放一枚铜板。”卫长昀对姜宁太过了解,“或者是一个储钱罐。”
姜宁无语地看他,“我是那样的人吗?”
卫长昀挑眉,“看来是我猜错了,不过我放的东西没什么新意。”
“没什么新意你也说说看。”姜宁懒得理他的调侃,追问:“不会你也没想好吧。”
“前一阵路过书斋,原本是想看看有什么书适合给小小、小宝平日里自学,却买了一支笔。”
卫长昀一直都有闲时路过书斋进去看两眼的习惯,“到时抓阄,便放一支笔。”
闻言姜宁立即明白他的用意,若是以文房四宝或者书为主,便是想让孩子走他的老路,与他一样以科举为径,步入仕途。
然而换成了一支笔,便不一样了。
提笔能写文章亦能作画,再广泛一些,还能记账、写戏文,不受限于读书科考,只想他笔下所写是心中所想。
“那我放一锭银子,是不太好。”
姜宁低咳一声,“太爱财了。”
“并无什么不妥。”卫长昀虚扶了他一下,等上完台阶才道:“有财方能人心安定。”
说话间,他俩走到了内院,正欲先回房换身衣服,就见春娘抱着孩子过来。
春娘向他俩颔首示意,“大人、东家,你们一回来小桃就跟我说了,我想着难得你们一起回来,时辰又早,便把小少爷抱过来,怕你们惦念。”
姜宁伸手去接,“谢谢春娘,想得这么周到。”
春娘道:“不敢不敢,只是我该做的,小少爷已经是难得的好照顾了。”
卫长昀看眼姜宁怀里的幼安,“外面风大,孩子我们待回房里,你先回屋吧。”
“是。”春娘微微躬身告辞,“才喂了羊奶,大人和东家缓些时候才喂。”
姜宁怕外面风吹着孩子,先一步进了房门,“晓得了,春娘你快去歇着吧。”
卫长昀向春娘点了下头,跟在姜宁身后进了房间,顺手把门关好。
难得忙里偷闲,他俩换了身衣服,便把幼安放到床上,一块坐着哄孩子玩。
厚实又柔软的被褥铺着,加上他俩都看着,孩子爬来爬去也摔不着。
就这么点大,连爬都还在学,更别说走跟说话了,只能咿咿呀呀地发出些音节。
陪着玩了好一会儿,不知道是累了还是困了,幼安自己寻了个地方趴着,没那么闹腾。
姜宁口渴,下床倒了杯水喝,往床边看去,见卫长昀比审了一晚案子还累,不禁偷笑。
难怪人家都说,带孩子比工作还累。
一家人难得凑齐吃一顿晚饭,坐在暖房里聊了好一会儿,等到亥时才各自回屋睡觉。
姜宁把幼安放到床里侧,自己睡中间,卫长昀睡最外面。
他睡着时,看见卫长昀还在点灯处理公务,轻声说了两句话,便侧身面朝着孩子睡过去。
不知道睡了多久,迷迷糊糊间,忽然被摇醒。
姜宁嗯了声,眼睛没睁开便问:“出什么事了?”
卫长昀单膝跪在床上,倾身朝里,“幼安脸颊有些烫,像是在发热。”
哪怕话里不确定,语气却已经是肯定。
姜宁几乎瞬间睁开眼,一个激灵想坐起来,被卫长昀扶住。
姜宁连忙伸手去摸孩子的脸,发现是有些烫。
可有的孩子天生体温就是要热一些,他不敢确定,又低头用嘴唇和额头去试。
烫。
不管是怎么试,都很烫。
在几位皇子面前都不曾慌张的姜宁,意识到幼安在发烧后,这会儿手却在抖。
姜宁强行镇定道:“去、去请大夫。”
“你先给他把身上的衣服解开,换身干爽的,我——”卫长昀顿了下,“不会有事的,我立即去,你别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