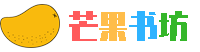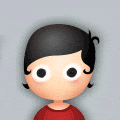做生意,尤其是吃食生意,便宜大碗就是硬口碑,都不用自己揽客,自有人帮你口口相传。
姜记食肆原本生意就好,镇上大多人家在外做工,或者家里不开火,便都会到这里来。
尤其对比那两家酒楼,来食肆吃饭的未必去得起,但去得起酒楼的,食肆这点饭钱都是小钱。
如此一来,客量自然要大一些。
连着几日,听闻食肆上了新菜的客人都赶来尝鲜,每到中午和下午,五张桌子全都坐满。
姜宁忙得团团转,一篓一篓的菜煮好了往陶锅里放,又端上桌,再去做蘸水。
好在菜都是提前洗好,而且每份都有卫长昀和朱红帮忙装,加上火锅能自己煮,只要不是太忙的时候,还能坐着歇会儿。
生意好起来,姜宁每天累归累,心里却踏实不少。
从去年开春做生意到现在,前边的那些日子还算清闲,可没攒下多少。
到后面忙了,银子攒了些,可又都花出去。
现在手里能有三十两,都是多亏了生意还不错,但凡差一点,家里财政都得赤字。
眼瞧着就到腊月,姜宁和朱红顾着食肆的生意,卫长昀又恢复了之前的作息,一天里大半的时间都在看书。
腊月一到,春闱便近在眼前,只有短短两个多月。
读书之事不可荒废,一日不读,便能落后别人不少。他虽天资高,可若不努力,持之以恒,迟早要败在天资自负上。
夜里食肆收了摊,卫长昀都还未从房间里出来。
姜宁看朱红做好了晚饭,过去帮忙端菜,“不用叫他出来吃了,我给他拿进去。”
朱红低声问:“那你们自己在房里吃吗?还是你跟我们一起吃?”
姜宁想了想,“跟他一起吃吧,好歹还能说几句话,不然跟他在私塾里有什么区别。”
在家里,总不能跟在私塾的宿舍里一个样。
闻言朱红点点头,“那行,你夹了菜就拿去房里,我们就在烤火房里吃,一会儿你们吃饭,拿到厨房里,我来洗就好。”
姜宁嗯了声,“要是太冷,明天洗也行。”
才进腊月,夜里的风都像冰刀子似的,刮脸上都疼,更别说大晚上在厨房收拾。
“厨房里有什么冷的,灶里的火还烧着,比外面可暖和。”朱红病了一场,养好了些,但人还是瘦了些。
不过养得好,气色倒是不错。
“那阿娘看着办,我把菜拿过去,不然两小鬼又要喊饿了。”姜宁嗔道:“难怪都说半大的孩子两张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吃饭香说明胃口好,身体也好。”朱红失笑,“你小时候吃饭就不香,还挑食。”
姜宁一点不反驳,“我现在还挑食呢,不爱吃心肝脾肺肾,腥味好重。”
姜宁觉得这根本不叫挑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味觉系统,很多东西吃起来味道压根不一样。
折耳根还有人觉得是死鱼的味道,但他吃起来只有微苦的草味。
他把菜端到烤火的屋子,炉子还是以前那个,防护网也没撤走,就怕是不小心碰到炉芯外壁,烫到哪儿。
卫小宝听到姜宁进来,立即从凳子下来,“宁哥哥,我去叫二哥吃饭!”
“哎哎哎,回来,他在看书,不叫他。”姜宁两只手都端着碗,连忙叫住人,“我一会儿给他送去。”
卫小宝啊了一声,“二哥闭关了?”
卫小小纠正他,“这不叫闭关,这是用功读书,人家说的是挑灯夜读。”
“是吗?”卫小宝走回来坐好,“唉,那个大叔好像要走了,说是回乡过年。”
姜宁听得糊涂,问道:“什么大叔?”
卫小小立即解释,“桥边的茶馆里请了一个大叔,每天都在那儿讲故事,我们这几天都一起去看,虎子、秀秀还有延舟哥哥。”
卫小小说的延舟是一条街上陆家的老大,下面有一个妹妹就是秀秀,今年十二岁,挺懂事又讨人喜欢的小孩。
因为年纪大一点,其他家小孩都爱跟他一起玩。
“还有一个月就要过年,人家当然要回去了,说不定年后就回来了。”
姜宁把菜摆好,“把碗筷拿出来。”
卫小宝听后,去旁边柜子把碗拿了出来,还有筷子,“那筷子要几双啊?”
“拿你们的就行,我跟你们二哥一起吃。”
“哦,那就是三双。”
卫小宝数出六只筷子,抱着三个碗回到炉子旁。
姜宁听他数数,不禁失笑。
前一阵两人学会了自己的名字,又开始学数字,从一到十。刚开始学那几天,都苦着脸,这两天才好些了。
姜宁待了会儿,等朱红把其他菜端来,这才离开。
走时不忘跟朱红交代,“阿娘,家里自己吃的碗筷,记得和前边食肆的分开啊。”
朱红点头应声,让他快去厨房拿菜,别一会儿凉了。
碗筷分开用是开食肆的时候,姜宁就特地分开的。
倒不是觉得客人有病,而是家里有两个小孩,餐具分开也是为了他们好。
大人身体经得起造,可小孩不一样,哪哪都要脆弱一些。
哪怕碗筷每日都是用开水煮过一回,可再好的消毒手段也毕竟有限,分开用客人放心,他们自己也安心。
姜宁往厨房走,经过房间时,看了眼窗户,而后搓搓手,心道等会再拿一个烤火笼进屋。
-
卫长昀手边放了一摞书,都是这几日看的,还有一叠自己写的文章。
太过专注,以至于姜宁推门进来时,他都没有第一时间发现。
是听到盘子放到桌上的动静,又觉得脚边有股凉气飘来,才反应过来。
放下手里的书,卫长昀抬头看过去,微微怔住,“我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
姜宁转头,“谁说是给你一个人吃的?我不是还得吃吗?”
闻言卫长昀呼出一口气,笑着起身,“怎么不叫我到外面去吃?吃饭要不了多少时间。”
“这一阵你都看书看得要魔怔了,夜里感觉你梦里都是这些策论、大学、中庸的。”
姜宁勾了一下凳子,坐下道:“反正在哪儿吃都一样,快坐下吧。”
卫长昀嗯了声,走到一边擦了手才过来坐下。
“等考完就好了。”
“那算起来,还得小半年呢。”姜宁拿着筷子,“学无止境,哪怕是考中,入朝为官怕是要学的更多。”
“但不必和现在一样。”卫长昀知道姜宁的话是心疼他,“要是落榜,那也能休息一段时间。”
春闱落榜,离下一次乡试还有两年、春闱还有三年。
人的意志再怎么坚定,也不能一直紧绷着。
姜宁点头,“那倒也是。”
日子还长着,日日都早也读晚也读,那才是真的走火入魔。
饭后卫长昀帮着姜宁一块收拾东西,把厨房整理了一遍,这才回房间。
各自点了一盏灯,房间里倒是比其他屋子都要亮堂些。
一个去记账,另一个就继续伏案看书。
卫长昀注意力集中,心思也都在书里,看完了半卷,才抬起头,捏了捏眉心,让眼睛休息片刻。
以往他并不太注意,还是姜宁提醒,让他看半个时辰书,便记得抬头四处看看,望远一点,这样对眼睛好。
尽管不知是什么原理,但卫长昀尝试过后,眼睛是会舒服一些,便成了习惯。
床榻那边静悄悄的,卫长昀一边捏着眉心一边转头看去,就见姜宁伏在桌旁,似乎累得睡着了。
卫长昀起身,走过去弯腰轻轻拍了下姜宁的肩,“去床上睡,这里趴着容易着凉。”
姜宁迷迷糊糊地唔了声,“我睡着了?”
卫长昀看他困得厉害,伸手把他抱起来,姜宁也不反抗,顺势往他怀里靠。
姜宁在他怀里蹭了蹭,道:“好困啊。”
“什么时辰了?你要不要一起睡,最近你都睡得好晚。”
无意识的撒娇,让卫长昀说不出拒绝的话。
时辰倒是不算早,都已经亥时了。
“陪你一起睡。”
“那你不要等我睡着了又起来看书。”
卫长昀失笑,看了一眼烤火笼,又瞥眼炭盆,把姜宁放到床上,“不会,你先躺倒被子里,我去把炭盆和烤火笼放好,免得夜里烧起来。”
姜宁含糊地应声,裹紧被子里。
卫长昀给他拉好被子,把东西放好后,又去盆架旁洗漱。
正打算吹灯回床边,忽地外面响起一阵敲门声,咚咚咚的,敲得很急。
卫长昀一怔,停住动作竖起耳朵听。
不过片刻,敲门声又立刻响起来,不是敲错门,或者是幻听。
卫长昀拿起一边的衣服披上,看向床上的姜宁,见姜宁侧身往窗外看,便道:“我去看看,你别起来了,容易冻着。”
姜宁有点担心,但看卫长昀拿了门边的棍子,便点了点头。
“你小心一点。”
卫长昀答应一声,拿着棍子开门出去,穿过院子往门口走时,同样被吵醒的毛栗跟在他脚边。
见状他笑了笑,对毛栗低声道:“先别叫,等会吵到其他人。”
毛栗从小就养在家,一家人把它当小孩样,平时总跟它说话,倒是听得明白。
卫长昀走到门口,朝外道:“不知深夜到访所谓何事?”
“是、是姜宁表哥家吗?我姓周,是他表亲,家里遭难才来投奔。”
卫长昀一愣,正要询问,就听到朱红的声音。
“二郎,是谁大半夜敲门啊?可是官府衙门,还是村里的人?”
朱红披着衣服过来,姜宁听到声响,自然也匆匆跑了出来,只有两个孩子还睡着。
姜宁走到卫长昀旁边,忙问道:“门外是谁啊?”
门外的人听到他们说话,又敲了敲,解释道:“姨母!我是周庚!”
刚过来的朱红一听是周庚,惊讶道:“周庚?你是三妹家里那孩子?”
卫长昀和姜宁对视一眼,迅速打开了门。
门才打开,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踉跄着跌进来,身上衣服褴褛,胳膊看着还有伤,还瘦得仿佛能看到身上骨头。
姜宁大为震惊,连忙弯腰去扶人。
卫长昀跟着把人扶住,姜宁便去关门,回身时看向朱红,“娘,这人你真认识啊?年纪比我还小。”
朱红上下打量着,点了点头,“我其实也只见过两三回,那会儿年纪比这小,可模子错不了,是你三姨母家的孩子,只是怎么会弄成这样啊?”
姜宁听她的话,确定是认得的人,便放下心来。
这大半夜的,要是不认识的人来敲门,不管是因为什么,到底怪吓人。
“这身上有伤,衣服还单薄,先给让他收拾一下。”卫长昀扶着他,要去哪间房时犹豫了下。
姜宁看出他纠结,出声提醒,“小宝已经醒了,正在那儿瞄呢。你去他屋里吧,我拿你的衣服给他换,你再帮他检查下身上的伤,看看哪里要上药。”
旁边朱红望着他们,心里一片疑惑。
自从嫁给姜大志后,她几乎不曾回过娘家,和家里人见面,大多都是在集上碰见。
这是怎么了?好好一个孩子,大晚上跑出来求救。
“阿娘,厨房里还有些吃的,你帮他弄点吃的,我估摸着饿了不少日子。”
听到姜宁提醒,朱红连声答应,连忙进了厨房。
姜宁看她进去,便回屋去拿衣服和找药箱,一边找一边琢磨这个周庚的来历。
是家里亲戚错不了,可平日里都无往来了,过年走亲访友也不见人影,怎么偏生遇到事,知道来他们这里投奔?
并不是恶意揣测,而是有些蹊跷。
他记得朱红娘家并不是永安镇的,是嫁过来。
她那位三姨母肯定也不在永安镇上住,否则没道理这么多年不往来。
所以周庚是怎么知晓能来这里投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