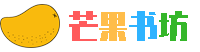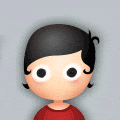官员俸禄过低,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已经算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了。
大周朝开国之初,因为刚刚结束了一段长达二十余年的动荡战争时期, 导致百姓人口锐减、大量土地闲置,大周朝的开国皇帝为了迅速恢复民生, 只能选择轻徭薄赋。
轻徭薄赋自然是对的,对于一个新王朝的巩固以及百姓对新王朝的认同感都会在这一个政策中受到极大的支持,可是轻徭薄赋的背后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央财政收入的减少。
周高祖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 想出来的办法是缩减宗室开支, 减少官员俸禄,以及开展军队的屯田制度, 规定两成士兵用于作战训练,八成屯田, 减少中央对军费的支出, 让他们能够达到自给自足,在此同时许多基础设施的建设也相对应地减少投入或者是暂缓建设。
各种政策一起下来后,大周朝确确实实缓解了财政的窘境,政府机器可以顺利地运转下去。
当时的大周朝的官员俸禄, 主要是有两块组成, 一块是货币, 另外一块是粮食和布匹, 因为当时的大周朝货币储备量太差, 银铜矿开采不足,所以不得不通过两种俸禄的发放方式来进行发放。
这样的情况下, 虽然大周朝开国之初定下来官员俸禄是偏低的,但是只是相对上一个朝代而言是偏低,实际上官员阶层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
就拿一个最基层的七品官举例, 一般而言进士出身后,若是下放地方便是七品县令,这是大周朝正统官员体系中的最坚实的基础官员行列,他们一年可以拿到九十石的粮食,以及二十两的白银,同时还有布匹等物的发放。
也就是说一个月这个七品官可以拿到7.5石的粮食,足够八口人吃一个月,同时在那个时候货币的购买力是惊人的,一两白银可以购买三石的上等大米,若是换成粗粮只会跟多。
可以说,俸禄方面确实不能说是发家致富,但是养活妻儿老小不成问题。
然而,随着大周朝的逐渐稳定,金银铜矿的开采变多,再加上大周朝与海上贸易之国来往频繁,大量的白银涌入到了大周朝,虽然大周朝如今也恢复了生息,但是小农生产的低效率,导致产品并未随着金银货币的极大增多而增多,那便开始出现了通货膨胀。
换句话说,就是钱不值钱了,以前一两银子可以买三石大米,现在一两银子或许只能买两石或是更少的大米了。
然而,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先帝时期,取消了粮食布匹发放给官员作为俸禄的方式,为了方便运输以及统一管理,先帝下令,将这些本该发放给官员的粮食布匹统一折算成银两进行发放。
在当时,肯定还是多折算了一些的,所以双方都觉得得利。
朝廷觉得自己省了许多运输调配上的事情,甚至就是原本需要专人进行仓库的管理和运输的看管上,都减少了人员支持,同时安全性也大大得到了增加。
往年,总有各地来报禄米仓出现走水或是因为雨季泛滥而有折损的事情,甚至还有在调配押运途中出现翻船事故的,好好的一船禄米,最后被打捞起来后数量肯定对不上了,就是打捞上来,也只能匆忙折价卖了,再买新米,这样的事故屡禁不止,再如何小心,每年总有几起。
官员们在当时也觉得自己得了实惠,总的俸禄没有变低反而变多了,而且更加自由了。
有些官员家中本就有许多良田,粮食自家的都吃不完,又从朝廷里领回来一堆,自家吃不完,还要想办法卖出去,一来一去,倒不如直接给银子来的痛快,他们也便利。
原本这个改制大家一致赞同,受到了所有官员的交口称赞,但是当时的官员们都没意识到,四十年后,事情又一次发生了改变,银两不值当年那个价格了,又没有了硬通货粮食布匹作为俸禄之一来进行发放后,他们的俸禄细细算下来,竟然至少比开国时候又少了一半!
本身开国时期时便是低俸禄,如今更是低俸禄中的低俸禄,让这些中下层官员如何存活?
这些读书人拼了命的想要读书进学,科举入仕,可不是为了来当穷官的!
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那般利欲熏心,也有季长歌、陶云亭之流,不管其他方面如何,多年来一直坚守着底线的,可是更多的人也是被逼无奈,为了更快更好地往上爬,只能跟着同流合污。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永嘉帝对于贪腐厌恶彻底,但是却抓一批、杀一批,屡杀不尽的原因之一。
确确实实,朝廷也将那一部分中间摇摆的官运推向了对立面。
翰林院中季长歌在日讲之时当场晕倒的消息,更是一下子被宣扬了出去,甚至他家中如何贫困、多年来如何兢兢业业做个好官,真实事迹已然是脍炙人口了。
因着季长歌在翰林院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存在,大家扒不出更多有用的信息了,甚至还有很多事迹,都是季长歌没有做过的,大家也是添油加醋地往他身上堆。
因为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只有季长歌够惨够穷够清廉正直,那么此次俸禄改制成功的希望才越大。
季长歌一下子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在官场上从查无此人的状态,一夕之间变成了百官楷模,溢美之词不胜言表。
而季长歌的所作所为,也确实经得起众人拿放大镜去看。
在公事上自不必说,翰林院里的人在没有进入实权部门之前,本身就是个清水衙门,季长歌这样的寒门出身的进士,根本连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机会都没有;而在个人生活上,季长歌是真正做到了无可指摘!
他如今住在城南的一个一进小院中,四周都是京城普通百姓,为了节省开支,宅院赁的还格外逼仄,家中只有老母亲、妻子和刚满七岁的女儿,什么仆妇成群、什么豪屋雅舍,和他们家根本搭不上边。
而从左邻右舍中传出来的消息,季翰林的老母亲和妻子日日在家绣花补贴家用,前一阵子天气太冷,季翰林老母亲得了一场严重的风寒,季家甚至将家中的两套厚棉衣都典当了,就为了凑齐抓药的钱,算算时间,岂不就是季长歌最需要用钱的时候,翰林院那边还砍掉了一众补贴,俸禄还欠着要到年底再发,他实在是已经走投无路了!
家中已然断了炊。
永嘉帝坐在御案后面听着锦衣卫指挥使张清泰的汇报,这份汇报很细,差不多是将季长歌的生平都重新查了一遍,就是季长歌的母亲和妻子每个月能靠绣花挣多少钱,卖往哪个铺子,多少天去一次,都调查的清清楚楚。
和秦之况呈上来的折子,几乎没有任何出入。
帝王的疑心病总是很重的,永嘉帝也想过,这是不是秦之况和季长歌设下的苦肉计。
可是面对这样的季长歌,永嘉帝也动容了。
他甚至开始反思,这些年来,是不是自己真的心太冷太硬了,没有去好好体察中下层官员的难处,只揪着朝堂上的高官们和他们斗智斗勇,觉得满朝文武都可恶,都有自己的小心思小伎俩,却忽略了还有一些人,是真正的将国家律法深刻在自己的心中,是真正忠君爱国之士!
他们或许如今官位还低,或许还不能像季长歌一样走到他面前的机会,但是他确实不该就忽视了这群人啊!
一样米,养百样人,同样是当官,却截然不同。
这些年来,这些官员不是没有提过增加俸禄之事,但是永嘉帝从来都是以“祖宗家法不可违”作为借口驳回。
这是因为永嘉帝认为,这些贪官污吏已经是怎么杀都杀不尽了,已经搜刮了如此多的民脂民膏,他们凭什么还要得到更多的优待?
莫不要以为皇帝就不懂人情世故了,他的锦衣卫在暗中监察百官,又让亲信抄过几个国蠹的家,抄出来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甚至很多他们家中的摆件古董,比他宫里的品质都要好!
这让一国之君的永嘉帝如何能忍?
原本永嘉帝想的是涨一涨翰林院的俸禄也没什么,翰林院拢共也就几十个人,这点多出来的俸禄,永嘉帝根本不当什么。
可是现在,文武百官都要求涨俸禄,这是要重新衡量各个职级官员的俸禄,是要改制,永嘉帝就不乐意了。
这些年来,虽然永嘉帝自认为已经够励精图治了,但是国库依旧吃紧,每年各处都要花钱,尤其是自他上位以来,大周朝各地天灾不断,夏季洪水冬季大雪都算不得什么了,好几次地龙翻身,严重到永嘉帝都不得不下罪己诏来祈求上天了,碰上特大灾年还有寅吃卯粮之事,如何还能给所有官员加俸禄?
这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费用,更不是一次性的开销,此乃长远之计,永嘉帝下不了这个决定。
而就在这个时候,清醒过来的季长歌再次上了一道至关重要的折子,这道折子一经公开,底下呼声更大,就连皇后都在用膳的时候问过永嘉帝此事。
季长歌的这道折子的名字便是《俸禄与廉政五思书》,深刻说了自己这么多年面对低俸禄,但是又想要高质量地完成朝廷交代事物时的各方面的思考,得出的结论是,合理的俸禄分配,可以更加好的推动廉政的产生,避免很多官员不得已地误入歧途。
这样一道折子,可以说是直接拉下了低俸禄却对官员道德水准高要求的遮羞布,永嘉帝看完折子后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恼意,有些下不来台,对季长歌这人是又爱又恨。
若要增加他们这些官员的俸禄,在每年税入不变的情况下,就需要从其他地方俭省下来,那么从哪里省?永嘉帝知道,动了谁的利益都要被反噬,如今朝堂已经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做皇帝的,也苦恼。
就在这道折子被呈上的第三天,太子周承翊面圣,恳求皇帝削减其明年大婚的开支。
周承翊明年二十又四,即将迎娶东宫正妃,这个正妃是永嘉帝千挑万选给太子定下的,家世、容貌、品行无一不是顶尖的,明年年满十八,就将入主东宫。
所有人都明白,这是未来国母的标准。
不过也没人说什么,毕竟太子是先皇后嫡出,刚一出生时永嘉帝就大喜,为了给儿子祈福,直接大赦天下,只可惜先皇后在儿子三岁的时候就驾鹤西去了,永嘉帝悲痛欲绝的同时,办完了先皇后的丧事后就封了年仅三岁的周承翊为太子。
先皇后嫡出的太子身份,无可指摘。
周承翊从三岁便是太子,如今已经当了整整二十年的太子,他从十八岁开始观政,虚心学习处理各种政务,在永嘉帝身体有不适的时候监国,这些年来,他做的面面俱到,太子地位无可动摇。
同时,所有人都能看到永嘉帝对太子的偏爱,太子大婚,永嘉帝准备拨银五十万两,同时将他内帑与国库中的许多名贵珍品、金银珠宝等作为大婚的贺礼,礼单长到让礼部撰写的人咋舌,甚至为了准备明年的这场大婚,礼部、太常寺、鸿胪寺、户部、宗人府以及东宫辅臣等经常要聚在一起商讨各种婚礼细节,京城中的珠宝甚至因为这场马上来临的盛大婚礼,出现了价格的极大上涨。
哪怕有人觉得这有些过分奢靡了,但是他们也说不出来。
毕竟这是太子大婚。
太子的地位稳固,十有八九就是下一任的皇帝,谁想要下任皇帝还没上位,就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不好的印象了?是在官场上不想混了吗?
然而,今天太子周承翊直接和永嘉帝进言道,希望永嘉帝能缩减掉他大婚一半的费用,用于支持官员俸禄改制。
永嘉帝闻言先是欣慰,后是生气,瞧瞧这帮子人,都将他最珍爱的太子都逼到这个份上了,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做的?
见永嘉帝面露不愉之色,周承翊诚恳道:“父皇,儿子本就觉得这场婚礼太过奢靡了,若是能削减掉儿子的开支,让父皇不要为难,这便是儿子的孝顺了,还望父皇成全!”
太子周承翊拱手行礼道。
这么多年父子两人之间的感情极深,深到让周承翊丧失了警觉之心,当他察觉到朝堂中对于此事的动向后,就想要为他父皇排忧解难,并未深刻去思考,他这般做,是否有收买人心之嫌?
嗯,太子大婚的开支都缩减了,就是为了给官员们多发俸禄,你们猜众人感激的会是永嘉帝还是太子?
好在此刻的永嘉帝也没有深思这些,并且他是深深信任着太子的,只觉得这件事让自己的太子受了委屈:“太子,可是你也知道,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哪怕是拿你大婚的银子一半出来,也只能支撑个两年,那之后的钱数又从何来?”
永嘉帝招手让周承翊坐在自己身边,这是天下无人可有的殊荣,只有太子周承翊是可以从小在他父皇膝头、龙椅上坐着长大的,周承翊从善如流,坐到了永嘉帝的身边,看着永嘉帝因为操劳国事而日渐生出的白发,握着永嘉帝的手诚恳道:“父皇,能支撑两年儿子已经很高兴了,两年内只要让底下官员更加勤勉办事,知道我们皇家的仁义,如何不能将这些银子给多出来?况且,这般一来,就更没有贪腐的理由了,若是银子多不出来,那就必定还存在着人心不足的巨贪,到时候父皇宝刀落下,就不怕他们不将银子吐出来!”
永嘉帝激动地拽紧了太子的手,忍不住连声赞叹三个“好!”,他着实没想到,太子已然成长到了这个地步,明白了朝堂之上的制衡之道,甚至还将目光放到了两年以后。
他的太子啊,仁义和谋略俱在,以后将天下交给他,再没有不放心的。
父子两个细细商量了一番,等到快要掌灯时分了,永嘉帝才拉着儿子的手一同去用膳。
第二日,永嘉帝就在朝堂上正式回应了此事,规定七品到四品的所有官员俸禄翻一番,而四品以上的官员,则是比以往多发一半的俸禄,饶是如此,也足够让人惊喜了。
很多人以为,这次俸禄改制最终惠及的是中低层官员,没想到他们高官之列也同样有了增加。
没人嫌弃钱少,况且这还是官方发钱,来路最正当不过的。
大朝上,永嘉帝鞭策群臣尽心尽力,共同为大周朝的天下而奋斗,而朝会之后,一向算是低调的秦之况这次却成了众人追捧的对象,便是首辅杨允功都走过来拍了拍秦之况的肩膀,看重之意不言而喻。
秦之况只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养成的低调涵养都要快破功了,嘴角上扬的弧度如何都压不下去,他这次,可谓是大获全胜!
在这场明争暗斗之中,有赢家就有输家,原本站着大义的赵潜回到户部之后,就被殷侍郎叫过去狠批了一顿,直言他做事陈腐、不知变通,让他回去之后好好反思,甚至将他目前手中的活都转交到了他同僚手中,一时之间,赵潜只觉得芒刺在背,其他同僚对他避之唯恐不及。
而刘守亮那边更是被秦之况直接动用关系,让人参了一本,挑出了他收授贿赂,动用关系安排赵潜升职一事。
这简直就是瞌睡就来了个枕头,永嘉帝因为太子受的委屈正要杀鸡儆猴呢,这只鸡自己就跳了出来,永嘉帝直接将两人一撸到底,贬为了庶民,且下的判决令上说的很明显,你们既然拿了高俸禄,以后再想动些歪脑经就要好好掂量掂量,永嘉帝的态度十分鲜明,那就是严惩不贷!
其他不明就里的官员尚且心弦绷紧,然而知道的人则是一切只在不言中。
秦之况在翰林院这么多年,怎么会一点感觉都没有,刘守亮掩饰的再好,细枝末节中总有泄露的地方,若是秦之况一下子被难为住了,抽不出精力去调查也就算了,而如今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秦之况自然是要顺着赵潜这条线深挖进去,动用了所有的人脉关系,如何能挖不到根?
不仅仅刘守亮和赵潜被打击到了,便是赵家也进入了秦之况的视野范围之内,心中恨上了。
打击报复完政敌,还要论功行赏,这次整个局中,功劳最大的人,非沈江霖莫属。
秦之况以前只以为沈江霖六元及第,在读书一道上天赋卓绝,但是在为官之道上还有的学,可是他万没想到,沈江霖在官场之上根本不像一个新手,甚至于一开始的时候沈江霖只是和他说用季长歌为棋子,让陛下知道他的难处,而后来的联合其他低阶官员汇聚的部门一同上奏,一直到最终盖棺定论的季长歌那封奏折,全部出自沈江霖之手。
一个人想出一个计策不难,可是沈江霖的计策是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秦之况甚至如今再往前复盘回去,已经完全明白了沈江霖的用意,他在给他说出第一个计策的时候,已经想好了后招,一盘天大的棋局,居然出自一个刚刚入翰林院三个月的新人之手,若不是秦之况是亲历者,别人告诉他的话,他或许都只会当作笑话来听。
而更加让秦之况心惊的是沈江霖的定力。
在这盘撬动了内阁、六部、五寺,甚至是皇帝、太子的棋局中,沈江霖一直稳稳的隐在自己的身后,不争不抢,定力稳的可怕。
这份心智、这份定力,秦之况只在内阁首辅杨允功身上见到过。
秦之况心中不经庆幸,好悬自己和沈江霖是同一战线的,若是沈江霖在政敌那一边,或许这次已经到了万劫不复之地。
因为这次直接收拾了刘守亮,刘守亮的下属崔焕便投诚了,投诚之物是刘守亮这么多年搜集自己的诗作文章,里头有好几篇都是自己私下之作,不知道如何就落到了刘守亮手中,其中有几篇里不乏自己对时政的针砭时弊,有对皇室不满之意,虽然那些已经是早年之作,可若是被放到了皇帝的案头,秦之况心中暗忖,以陛下的气量不太会直接治罪,但是调离京枢,明升暗降是绝对的。
若是刘守亮更狠一点,还有后招,自己或许下场更惨!
因此种种,秦之况对沈江霖看的极重,已经打定主意,要好好推举一番沈江霖。
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