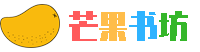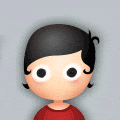季长歌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十分慌乱。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答应下来秦大人的请求到底是对是错,但是事情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再想反悔也绝无可能。
再说了, 如何反悔?反悔什么?
即便秦大人不让他这样做,这般下去, 他最后的结果不也是如此吗?如今只不过是秦大人要将他推到幕前,提前将这个结果爆出来而已。
季长歌不住地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
他今年已经三十而立了,在翰林院蹉跎了六年, 哪怕只要交代他的事情他都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去做, 从无半点错漏,可是他本就出自寒门, 妻子也是糟糠,并于任何后台, 也不得上面看重。
一开始进入官场的时候季长歌有如此多的雄心壮志, 忠君爱国、廉政爱民的想法时刻充斥在他的脑海与心中,一刻都不敢忘记。
然而,六年岁月,两千多个日日夜夜, 重复地去做一些是个读书人都能做的活, 再多的热情、再大的热忱, 也渐渐熄灭了, 他终于开始思考, 只凭着一腔热血,自己究竟能不能在官场上有所作为?
当秦之况找上他的时候, 他的内心不是不抗拒的,因为这违背了他一直以来内心的坚持,可是秦之况只告诉他一句话:这是你在官场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甚至是唯一的一次机会。
季长歌已然明白, 这世上努力的人有许多,有天份的人也有许多,可是机会却是稍纵即逝的,抓住了就是抓住了,抓不住便会一直往下落。
季长歌这样的人,其实是个狠人。
他能忍受极致的清贫,如此克己复礼,那么当他下定了决心去做一件事的时候,谁都拦不住他。
他妻子眼睁睁地看着他,三日来滴米未进,只喝白水,不管她如何哀求,季长歌只是摇头。
王安引着季长歌进入“养心殿”的时候,心里还嘀咕:怎么今日秦大人选了这人来讲学?
永嘉帝想做明君,但是哪怕是明君,在一些小事小节方面还是有自己的偏好的,皇帝听日讲,本身就是一种姿态,有时候遇上口才不错、妙语连珠的还愿意听一听,遇到一些照本宣科的,则是只顾自己翻看手头的折子,并不理睬。
这季长歌只进宫讲过两三回,显然不是受永嘉帝待见的,否则永嘉帝自己也会亲自点人。
果然,等季长歌诚惶诚恐地进了“养心殿”,永嘉帝的眉头就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不过永嘉帝的气量依旧是可以的,季长歌行过礼之后,永嘉帝语气平和地让他起身。
季长歌起身的时候腿软了一下,差点没站起来,等站稳后才请罪道:“陛下赎罪,下官久不面圣,实在是有些过分激动了,倒是让下官差点失仪。”
永嘉帝没想到季长歌这次说话机敏了许多,也没追究他的失仪,只让他开始进行日讲。
每年二月到五月,八月至冬至,翰林官都会轮流进宫给皇帝和太子进行日讲,也便是春讲和秋讲,一般春讲探讨四书五经中的微言大义,提醒上位者要以德治国;秋讲则是以史为鉴,以古证今,从既往朝代中发生过的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拿出来讨论,帮助上位者规避一些已经发生过的历史错误,更有经验地治理国家。
除了日讲外,还会举行经筵,皇帝带领核心文臣官员入“文化殿”进行听讲,一般由内阁或是翰林院主持,届时出席的人就更多了,不过这样的经筵一月只有一次,像季长歌这样的身份还不够资格主持这般重要的场合。
永嘉帝起身坐到了御案后面,季长歌站在日讲桌前,翻到今日要讲的是王莽当政期间的这段历史。
永嘉帝一开始并没有当回事,这段历史早就有人给他讲过几遍了,王莽这个人物也是彻头彻尾的负面人物的形象,得不到后世一点好的评价。
否则白居易也不会写下名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了。
王莽此人做大司马时,就诛杀异己,培植党羽,为臣不忠,等到他终于篡权夺位,称帝改号后,又出台了一系列乱七八糟的政策,导致名不聊生,处处生灵涂炭,最后被绿林军所杀,总共在位才十五年,他的朝代他的一切便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汉书》中评价王莽为“逆臣”是“巨奸”,因为在古代文人心中,皇位的继承是需要得天而授的,是需要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的,否则皇帝为何又叫“天子”?
就算是以成败论英雄,唐时李世民可以发动“玄武门之变”,取兄代之,但是其后期施行仁政,大唐盛世由此拉开序幕,也算是挽回了一些名誉上的损失,而王莽当政期间,却是暴力镇压各地起义民众,最终导致人口锐减七成以上,这样的君主绝对算的上是暴君了。
每次日讲官讲这段历史的时候,便是提醒永嘉帝要在王莽身上吸取教训,一定要做一个仁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万不可丢失了民心、倒行逆施。
永嘉帝是一边看着奏折一边听的,听着听着,永嘉帝开始放下手中的朱笔,抬起头看向了站在日讲桌前的季长歌,被他新鲜的角度和想法吸引住了。
季长歌先是老生常谈了一番王莽的生平,批判了王莽的狼子野心,然后话锋一转,就说到了王莽新政中的可取之处,着重讲了“王田制”。
土地制度是每一个封建王朝的核心,每每王朝创立之初,随着旧式力的倒台,新势力的崛起,都会有大片的土地被新势力不断地兼并,可是等到了一个王朝的末期,土地不会再生产出来,大家为了得到更多的土地自然会激化矛盾,最终就会演变成战争,通过暴力手段将土地进行再分配。
故而三国开篇词就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然而王莽新政中,他的土改政策是将土地全部国有化,私人不再允许买卖,从根源上抑制土地兼并,这样的想法是非常有创意且深刻的,只是不符合当时的国情,反而最终激起了民怨,义兵四起。
季长歌说到这里的时候,永嘉帝的双眼灼灼,已经彻底丢开了折子,只专心于听季长歌所讲,他万万没想到,季长歌想问题的角度如此深刻,且说的都是他隐藏在心中多年却无法解决的问题。
大周建朝一百多年,许多阶级开始固化,科举取士原本为的就是打破这样固化的阶级,不让世家勋贵掌握所有的话语权,可是永嘉帝还是发现,慢慢地,寒门所出的进士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进士依旧出自世家和勋贵之族,这如何不让他心中烦闷?
且这些家族手中的土地也变得越来越多,有土地就有民众,有一句话说的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照理这天下的土地都该是皇室的,可是真实的情况呢?皇家拥有的土地有多少?那些世家加起来共有的土地又有多少?
虽然季长歌是在谈古,可是永嘉帝从这段谈古中很容易就联想到了如今大周朝的局面。
季长歌擦了擦额头上的虚汗,继续道:“故而,王田制度是有其优越性的,只是……”
季长歌停顿了下来,永嘉帝有些不满地催促:“季爱卿,接着往下说啊。”
同时,永嘉帝也看到了季长歌额头上不断滚落下来的汗珠以及脸上有些不正常的红晕,这是怎么了?难道朕这个“养心殿”里的炭火太足了?把人热着了?
正想着要不要叫宫人撤下一个炭盆时,“咚”地一声,季长歌整个人直挺挺地倒了下来,把永嘉帝吓了一大跳!
王安同样也是惊呼了一声,外头站岗的禁军立即握住腰间佩刀在外头高喝:“陛下可有碍?”
王安连忙打发了小太监和外头人说无事,然后迈着小碎步将季长歌的人翻转了过来,验了验鼻息发现人还有气,连忙道:“陛下勿惊,季翰林只是晕了过去。”
永嘉帝放下了心,连忙让人传太医,又让人将季长歌抬到了隔间的脚踏上。
很快太医就到了,毕竟是专职服务皇家的医师,又是皇帝急招,来的还是太医院的陈院正,陈院正蹲下身子给季长歌把了脉,一把脉,陈院正甚至有些不敢置信,又把了两次,翻了翻季长歌的眼皮看了舌苔,这才收回了手。
永嘉帝只以为是什么急症,否则怎么好端端的人就晕了过去了呢?再看到医术最高明的陈院正把了三次脉,心里想当然的以为这个病症或许很棘手。
结果陈院正告诉他,无需开药方,估计一会儿季翰林就能醒过来,只是醒来后,务必给他吃点东西就好。
永嘉帝一开始还愣在了那里,整天日理万机、和群臣勾心斗角的皇帝,脑子里装八百件事,他都没听懂陈院正这话是什么意思,看着陈院正弯下腰行礼请求告退,他摆了摆手,等到陈院正都走出门了,才反应过来——陈院正的意思是,季翰林是没吃饱才晕倒的?
这是开了什么玩笑?堂堂朝廷命官,清贵六品翰林,当年他钦点的进士,会吃不饱饿晕?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
若是季长歌本就遭厌弃,或许永嘉帝还没这么愤怒,可是刚刚季长歌讲的极好,永嘉帝心中还想着以往竟是没有多听听季翰林日讲,以前蜻蜓点水听了两次后不召见他了,属实是错失了英才,不过今日再发现了也不迟。
结果闹了半天,季翰林还是饿着肚子给自己讲学的?
哪怕永嘉帝知道翰林的俸禄并不高,但是不至于就到饿晕吧?
瞬间,永嘉帝就开始阴谋论了,上官欺压、底层官吏被盘剥,今日还是自己看到了,若是没看到,岂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才就要被磋磨死了?
永嘉帝脸上的怒意一闪而过,他命人将季翰林给抬回去,同时赐了十道好克化的御膳给季长歌,好让他一醒来就能有东西吃,然后便让人急招秦之况入宫。
秦之况一听到永嘉帝有招,而且被叫过去日讲的季长歌被抬着回来的,众人不明所以,只觉得最近翰林院中到处都是腥风血雨、不太平。
秦之况虽然近日来连砍了下面人许多补贴之物,但是他自己又是个以身作则的人,并没有出现底下人受苦受难,自己却是在享受的情况,故而哪怕下面人再如何怨声载道,觉得上官不作为,也没办法真的面对面和秦之况叫板。
甚至有些人心底还是念旧情的,看到这种情况下秦大人被叫走,其实是有些担心的,毕竟秦之况这几年在翰林院的作为算是公允的,真的再换一个人,还不一定能比秦之况要好。
秦之况进了“养心殿”,便看到永嘉帝肃着脸坐在上首,等到秦之况行完礼,也不废话,直接就责问秦之况:“秦之况,你可你知道你的属下季翰林,刚刚来给朕做日讲的时候,居然饿晕了过去?难道翰林院的俸禄是不能让他们吃饱饭的?你这个上官是怎么当的?”
秦之况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先是“惊讶”了一瞬,沉默了一会儿后,秦之况慢慢跪了下来,将头上的双翅乌纱帽摘了下来,放到了一边,缓缓磕了一个头道:“还请陛下恕卑职已无法胜任翰林院学士这个官职,摘了卑职的乌纱帽吧。”
秦之况的行为完全出乎了永嘉帝的预料,一般面对这种情况,不都是应该自我辩驳一番,陈情甩锅才是正确解答方式,秦之况是在做什么?是不服气朕的指责,还是有何隐情是朕不知道的?
秦之况算不上最有能力的那一拨臣子,但是为人忠心、做事仔细,早前做事还有些固执己见,这些年来已经好上了不少,如今是老毛病又犯了?
永嘉帝很是头痛。
作为皇帝的永嘉帝,虽然是万万人之上,但是这天下太大了,不是他一个人可以治理的过来的,哪怕他手段强硬,治理了朝堂二十多年,和几个大臣你来我往勾心斗角了大半辈子,却依旧不得不承认,自己是需要他们的。
士大夫与天子,是共治天下的。
这样的觉悟是在永嘉帝与臣子们搏斗了十年后才得出的经验教训,以至于当有一些真正的能臣干吏有时候被他惹急了,准备撂挑子不干的时候,永嘉帝还不得不放下身段安抚,也属实算是明君的无奈了。
“秦之况,你有什么话直说便是,你我君臣多年,又何必这幅作态?”永嘉帝板着脸不愉道。
秦之况抬起头来的时候,老泪纵横,竟是哭了???
永嘉帝尚觉得有些诧异,便听秦之况哽咽着道:“回禀陛下,自从陛下提拔卑职为翰林院学士,掌管整个翰林院后,卑职是夙兴夜寐、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便是翰林院的其他人,亦是潜心治学、勤勉观政,翰林院的庶吉士们素有储相之称,是整个大周朝最重要的人才培养之地,陛下交托如此重任给卑职,卑职又岂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听到这里的时候,永嘉帝微微点了点头,这话不算错,这几年从翰林院输送出来的人才品质都算好的,不管是入得中枢还是下放地方,都有不错的政绩做出来,其中并不是没有秦之况的功劳的。
只是这和季翰林饿晕一事有什么关系?
然后永嘉帝便听秦之况接着道:“前一段时日,度支郎中赵潜到了翰林院来,将卑职提交上去的度支科目给驳了回来,因着卑职许多条目上多要了一些东西,与我们翰林院该有的份例合不上了,卑职与他争论了翰林院官员俸禄太低,所以不得不多要一些杂物来补贴他们,但是赵潜道,若是人人都能如此做,那么要律法有何用?要规矩有何用?卑职实在被他说的抬不起头来,只能删改了上交的度支科目,竟没想到发生了季翰林饿晕一事,是卑职没有体察下属的情况,是卑职的失职。”
秦之况越哭越委屈,一个大老爷们,竟是涕泗横流,拿出帕子擦了擦才能继续道:“可是陛下啊,翰林院这么多人,不是就季翰林一个啊,等季翰林醒了,您可以去问问他,卑职有没有帮过他?只是卑职的俸禄也没有多少,就是想帮,又能帮多久?又能帮多少?卑职这个官,实在做的艰难,倒不如,倒不如,哎!”
秦之况摩挲着手边的乌纱帽,眼里充满了不舍和内疚,跪在下面,久久不再言语。
若是沈江霖此刻在现场,绝对会竖起大拇指,对秦之况刮目相看了!
他终究是小看了他们的翰林院院长,这样拿捏人心的演技,不,都不能说是演技了,简直就是真情流露、内心剖白,面对这样的下属,就是心肠再冷硬的上位者,也会被牵引着站到他的位置去思考问题。
“陛下,卑职愧对陛下的栽培和看重啊,卑职有罪,还请陛下降罪!”秦之况终是将乌纱帽放开,再一次缓缓而又坚定地磕下头去。
永嘉帝起身,将秦之况扶了起来,又亲自将他的官帽戴好,心中从一开始对秦之况的苛责,到如今也是心有戚戚焉,原来这其中竟是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原来秦之况一个人苦苦扛了这么久。
永嘉帝一向自诩自己洞察人心,当了这么多年皇帝,是再也不相信有真正的纯臣忠臣,看来他还是误解了读书人的风骨,前有季翰林,后有秦之况,这些人,不都是在用自身说明着对国家律法的重视,以身作则,宁愿饿晕、宁愿被刁难,也依旧在自己的位置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么?
永嘉帝长叹了一声,拍了拍秦之况的肩膀,语重心长道:“秦爱卿,你说的朕知晓了,你做的很好,是朕过于心急了,看来翰林院的薪俸是太少了一些,以至于朕最重视的人才竟是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朕竟不知,而你们也瞒朕瞒的好苦啊,怎不早点上折子说明?难道朕还会为了区区几两碎银子,而难为你们?”
秦之况这下子是真的有些受宠若惊了,他虽是天子近臣,但是还从来没有得到过被皇帝亲自戴官帽的优待,甚至永嘉帝还似老友一般语重心长的和他说话,拍他肩膀的时候,秦之况觉得自己那边的肩膀都麻了一下。
再大的委屈,有皇帝此番的认可,也值了。
男人九分真一分假,演戏演到自我陶醉。
见秦之况又惊又喜,激动地嘴唇嗫嚅几下,却说不出话的样子,永嘉帝心底越发信了秦之况所言,背过手在殿中踱步了几下,然后突然站定,对着秦之况道:“秦爱卿,你回去之后就写一道折子呈上来,将目前翰林院中各个职级的薪俸和补贴的情况一一写来,另,帮朕调查清楚,季翰林是真的靠这点俸禄无法吃饱吗?这次,朕要亲自了解其中细则。”
永嘉帝不是那么好忽悠的皇帝,最后一句话又是习惯性的敲打。
秦之况对此早就有了心理准备,连忙跪地行礼,三呼万岁,高高兴兴地领命退去了。
有永嘉帝的一句话,何愁翰林院以后的俸禄和补贴不涨一大截?
秦之况所面临的翰林院内部的问题已经迎刃而解了,但是这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
随着翰林院上奏了他们中低阶官员俸禄过低的折子,闻风而动的国子监祭酒也上奏了他们的官员薪俸过低的情况,毕竟他们的情况和翰林院很像,都是低阶官员较多,然后便是太常寺、太仆寺、鸿胪寺三大寺同时上奏,期望永嘉帝对他们低阶官员同样进行俸禄改制。
这声势,一下子就浩大了起来!
许多京中低阶官员都蠢蠢欲动,没有人希望自己明面上的收入少,就算他们的上官无动于衷、不想趟这个浑水,可是奈何底下的人已经迫不及待了,裹挟着上官也要抓住这次机会上奏。
于是乎,先是油水最少的工部,然后是礼部,后来又是工部和兵部,纷纷闻风上奏,最后便是油水衙门户部、吏部也坐不住了,别人都上奏,就他们不上奏,不是明摆着告诉世人他们的油水足吗?
上奏,必须上奏,和光同尘才是为官之道!
一时之间,京城之中官员薪俸改制的呼声越来越高,最后不得不由首辅杨允功出面,代替百官呈奏,一场足以写入史书的官员改俸制浪潮就这样轰轰烈烈地掀起了。